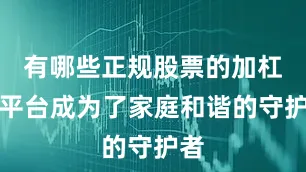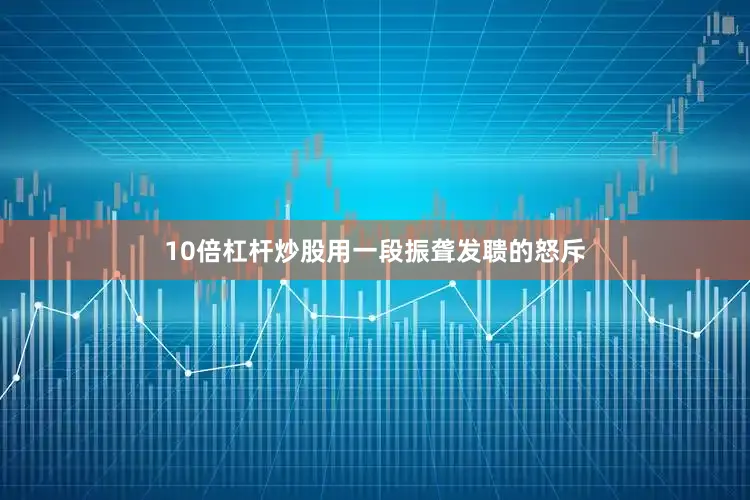李铁夫:朝鲜籍中共党员,反对王明错误被诬为“铁夫路线”
有两种人,一类是言过其实,这属主观主义的谬论。另一类则是脚踏实地,不热衷于空谈,充分考虑时间、地点与条件,这体现了唯物的、辩证的革命理念。刘少奇、李铁夫以及其他众多同志,便是这一理念的杰出代表。这番话出自1937年5月17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李铁夫同志作为河北省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以及白区工作代表的出色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由衷赞誉。然而,不幸的是,李铁夫同志因突发伤寒,经治疗无效,于同年7月10日不幸离世,享年36岁。
革命夫妻“假戏真做”
当张秀岩接到从延安传来的李铁夫病危的消息,心中不禁忧虑:丈夫李铁夫素来体弱多病,实在应当得到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从天津至延安,途中需穿越重重封锁线,幸赖地下交通线的助力,张秀岩迅速抵达西安。在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协助下,她搭乘一辆前往延安的货运卡车。然而,接连数日的暴雨使得原本坎坷不平的道路更加泥泞,卡车行驶缓慢,不时陷入泥坑,车轮亦需不时施以巧力方能脱困。待张秀岩抵达延安时,李铁夫已在三天前安葬。
“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即便她与他同行延安,他也未必会答应。这正如他们共同生活的几年,表面上是她在奔波,实则他才是主导者。

◆李铁夫与张秀岩,于1936年天津的地下斗争岁月中,留下了合影的珍贵瞬间。
1934年伊始,党组织派遣刚恢复党籍的李铁夫,化身为匿身于天津的使者。起初,他寄居于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邻近的26号路(今开封道)沿街的3号吴砚农宅。随后,依照党的指示,张秀岩与李铁夫这对年轻情侣开启了“住机关”的生活模式。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时代,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求,最佳的掩护方式便是男女革命者假扮成一对夫妻,共同生活,这种生活方式被俗称为“住机关”。张秀岩,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早在1926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曾与郭隆真等革命志士并肩作战。此次,她被调至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担任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一职。党组织为李铁夫在天津的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令他对外自称福建籍的“老杨”,而张秀岩则以南开中学教员的身份,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朱家胡同(今解放北路与曲阜道交叉口)一家裁缝铺楼上租赁住所,并假扮成夫妻居住。这位“老杨”身材清瘦,眼镜之下,面容文雅,寡言少语。相对而言,他的“妻子”则显得贤淑温柔,性情温婉,常面带微笑。这对“夫妻”给人留下了十分恩爱的印象,形影不离,出入总是手牵手。作为“妻子”的教员,在市场上采购食材时,会在暗中传递那位鲜少出门的“丈夫”与地下党的通信。而且,这对“夫妻”家中常迎来不同寻常的客人,那是地下党的同志们以探访亲友为名,在此召开会议、交流学习。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作为彼此尊重的同志,李铁夫耐心教授张秀岩日文和英文,张秀岩则为李铁夫搜集写作素材,并料理两人的生活起居。
在日复一日的共同生活中,张秀岩,一位出自名门望族的大龄未婚女性,逐渐从对远道而来投身中国革命的朝鲜青年李铁夫的敬仰,转变为深厚的爱情。李铁夫身患疾病,张秀岩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而当她患病时,李铁夫则凭借在日本的医学学习,为她查阅药典,寻觅良方。两颗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心,逐渐紧密相连。在党组织的批准下,他们终成眷属,结为夫妻。

◆张秀岩
自结为连理后,张秀岩在北宁铁路宁园图书馆寻得一份职位,月入仅二三十元。而李铁夫并无公开的职业,经济来源匮乏。两人的生计全赖张秀岩那微薄的薪水维系,日常饮食多为粗茶淡饭。尽管他们节衣缩食,但将大部分收入投入党的活动,并时常资助那些更为拮据的同志。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这对坚信革命必胜的夫妇,无时无刻不在细心关照那些同样投身革命的同志。从敌狱中获释的同志,往往一贫如洗。李铁夫曾将仅剩的一件大衣典当,以换取资金为出狱者购置衣物。失去大衣的李铁夫,在寒冬时节外出,只得身着棉袍。然而,这对革命伴侣依然秉持着乐观的革命精神,积极组织众人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他们的感召下,众多有志青年纷纷成长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张秀岩的侄子侄女们也相继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革命志士共赴一途
李铁夫,原名韩伟键,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求,曾化名为金元镐、胡国明、韩国李、云岗等。他于1901年,在朝鲜咸镜南道洪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诞生。日本侵略者强行占领朝鲜,并将其更名为“大韩帝国”,这一行径激起了无数如李铁夫般满怀激情的朝鲜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投身于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立志为民族解放付出一切。在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中,18岁的李铁夫不仅积极参与,更担任了领导者的角色。在朝鲜全国范围内反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集会上,李铁夫作为朝鲜学生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一员,站在成千上万渴望祖国复国的群众面前,激情洋溢地宣读了由代表们共同签署的《独立宣言》。面对逼近的日本宪兵,这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的李铁夫在众人的掩护下成功逃脱。日本警察署对这位无畏的学生领袖恨之入骨,对他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通缉。在国内已无法继续生存,李铁夫不得不流亡至中国。
1919年四月,李铁夫抵达上海,于《新大韩新闻社》谋得一份编辑职位。彼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正式成立,李铁夫与中朝革命志士并肩作战。为深入探寻抗日救国的真理,1920年,李铁夫化名潜行,秘密赴日本深造。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深造,潜心研读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四载光阴,学有所成,李铁夫重返朝鲜,以《东亚日报》、《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为掩护,投身于创建朝鲜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李铁夫是朝鲜马列主义同盟早期加入的共产党员之一。1926年春天,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铁夫当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随着斗争愈发惨烈,朝鲜共产党遭受重创,李铁夫亦再次被通缉。在共产国际的引荐下,他再度流亡至中国,继续投身革命事业。1926年,李铁夫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铁夫
1931年,李铁夫受中共委派,前往北平履职,担任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党团书记,自此开启了为期六年的波折重重的地方领导岗位生涯。次年9月,他相继出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然而,1933年,河北省委机关不幸遭受严重破坏。5月18日,在北平秘密召开反帝大同盟党团会议之际,李铁夫不幸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并被押解至南京监狱。幸得党组织和朝鲜同志的全力营救,同年7月15日,李铁夫终获保释,重获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的开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前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北方党组织遭受了重创,众多同志被捕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使得共产党在白区的势力急剧衰减。面对这一局面,理论造诣深厚且实战经验丰富的李铁夫深感痛心,他不愿看到党的利益继续遭受重大损失,亦不忍目睹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出于对党的高度忠诚和责任感,李铁夫于1933年10月至1934年2月间,相继撰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等文章和意见书,对河北省委工作中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李铁夫的文篇在党内流传,赢得了众多同仁的赞同。然而,在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势头迅猛,李铁夫的观点遭到推行者的强烈抵制,更被诬为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张秀岩因支持李铁夫而遭此连累,一同被剥夺了党内职务,与党组织断了联系。面对这一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的处理,李铁夫与张秀岩承受了巨大的思想压力。在深思熟虑后,他们坚信自己的理念对党和人民有利,于是并未气馁,反而相互勉励,互相支持。李铁夫以“仰望光明”四字自勉,深信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指日可待。这对夫妇胸怀赤诚,依然保持着满腔热情,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时刻准备着响应党组织的召唤。
任中共早期领导职务
吉鸿昌、南汉宸等同志身为中共的秘密党员,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于1934年5月,在天津成功创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势力的统战工作。为了揭露蒋介石政府的反动宣传,向爱国人士宣扬革命真理,向广大革命群众传播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天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李铁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其中,为吉鸿昌同志组织的爱国人士培训班授课。随着革命事业的高歌猛进,即便是在严寒的冬季,李铁夫与张秀岩同志也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抓的风险,深入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之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李铁夫同志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懈,而张秀岩同志则从自己拮据的生活费中省出资金,资助创办革命刊物,开展党的宣传活动。他们创办的《华北烽火》、《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等进步报刊,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催生了李铁夫、张秀岩等仁人志士积极投身于“一二·一八”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的发起和组织。他们挺身而出,勇立于游行队伍的先锋,与广大爱国青年携手同行,肩并肩站立。面对反动势力的刀光剑影和棍棒威胁,他们毫不畏惧,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向民众普及抗日救国的理念。
“只要我们与群众并肩作战,心怀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困难皆可迎刃而解。”正是得益于稳固的群众基础,李铁夫夫妇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能高效地推进工作。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北方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在逆境中未能审时度势,反而坚持采取激进的正面抗争策略。他们公然组织“飞行集会”,不顾后果地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导致党组织和群众运动频繁遭受破坏。众多党员被捕并为之献出了生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李铁夫对此深感痛惜。他始终秉持党在白区的严格工作纪律,坚守党的原则立场。始终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他笔耕不辍,冷静思考,对形势进行了客观的估计与分析。在此期间,李铁夫接连八次上书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力陈改变斗争策略之必要,其建议得到了河北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省委书记孟用潜的坚定支持。
中日民族间的矛盾持续加剧,抗日民主运动亦呈新一轮高涨态势。为了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的瓦窑堡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华北事变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以及抗日联军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批判了党内长期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被后人称为“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会址。
为全面传达和宣传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刘少奇于1936年春受中央派遣,抵达天津,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履新伊始,他即着手清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遗毒,确立了党的正确政治方向。他高度评价了李铁夫的观点及其在艰苦环境中的不懈努力,因此恢复了李铁夫的党组织关系,并任命他为河北省委委员及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与此同时,他还任命张秀岩为市委副秘书长和天津市委妇女部长。自此,针对“铁夫路线”的斗争得以有效遏制,李铁夫与张秀岩夫妇共同肩负起天津党的领导重任。
李铁夫接任天津市委领导职务后,充分发挥组织效能,着力发展党员队伍和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持续壮大革命力量,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为党在天津的工作开辟了崭新局面。他深知在白区开展党的工作,关键在于深入工人阶级和社会最底层,这是他工作的重要方针。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李铁夫不仅在一些工厂企业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还在工人集中的塘沽设立了区委。市委还积极组织群众,有力地抵制日货走私。李铁夫协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成立了党支部,并创立了“民众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凭借他对群众的深厚联系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天津的党组织和民先组织得到了显著发展。至1936年底,党员人数从不足十人增长至四百余人,民先队员增至七百人。为进一步强化全市学生工作,市委还特别设立了学生区委会。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态势。
英年早逝,浩气永存。
1937年春,党组织委派李铁夫前往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原本计划张秀岩也一同前往,然而,张秀岩鉴于天津党的工作正处于恢复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婉拒了组织的安排,毅然决然留在天津继续奋斗。谁料,这次离别竟成了这对革命伴侣永恒的诀别。
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大礼堂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会议由张闻天和刘少奇同志共同主持。李铁夫同志在会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讲话,对“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同志对李铁夫同志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华北党曾对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李铁夫同志便是其中的领袖。”在与李铁夫同志的亲切会面中,毛泽东同志对其及张秀岩等同志所遭受的不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此次会议上,党中央全面终结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并确认李铁夫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李铁夫同志并未因毛泽东同志的赞誉而自满,他向白区来的同志们表示:“在白区,我们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如今来到延安,就如同回到了温暖的家园,我们要努力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为劳动人民贡献更多力量。”
鉴于李铁夫身患重症肺疾,党中央审慎决定,暂时安排其留任陕甘宁西北局工作,以便在岗位上治疗休养,兼顾工作与健康。

李铁夫先生仙逝之际,其战友与家属共同撰写了纪念文章的手稿。
在李铁夫病情加重之际,党中央紧急向张秀岩发送了电报。当她不辞辛劳,日夜兼程抵达延安时,李铁夫的遗体已被安葬于清凉山之上,张秀岩终究未能与丈夫诀别。然而,她坚信,对丈夫最崇高的缅怀,莫过于投身于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张秀岩始终坚守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直至1968年辞世。
“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之墓”,落款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党中央还为他举办了追悼大会,《新中华报》也刊登了他的生平事迹。李铁夫同志的遗体被安葬于延安清凉山,其生平事迹亦收录于新版《辞海》之中。
李铁夫,一位朝鲜革命志士,却身居中共早期党组织的高位;他誓言为民族解放奋不顾身,将宝贵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这片华夏土地;他坚守真理,以正义和良知为笔,即使在囚禁之中,也始终坚定地与信仰并肩前行;他遵从组织调度,怀抱赤诚之心与张秀岩假扮夫妇,共同完成了使命,成为革命队伍中极为罕见的“跨国姻缘”;他以非凡的个性与绚烂的音乐,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浩然正气的赞歌。
2014年9月的尾声,李铁夫先生的墓碑正式在延安四八烈士陵园的围墙之外,烈士墓区启动了迁移与重建的工作。
胜亿优配-配资加杠杆-a股配资-网上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